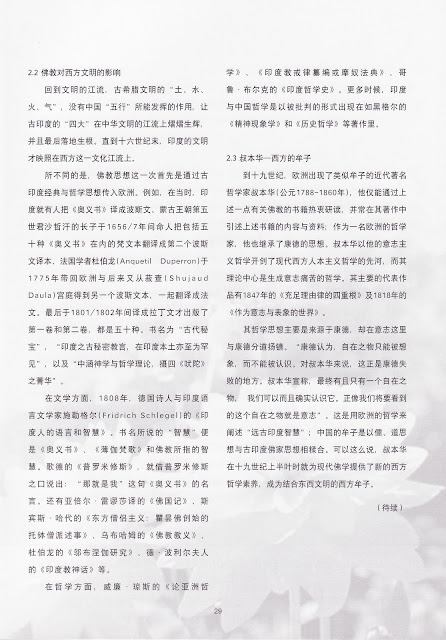导言
作为中华文明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就来源于印度。本文将对古印度的佛教文明经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来说明佛教文明与东西方文化如何的磨合及形成过程、其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以及对和谐世界所起的映照作用。
为了读者的方便,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含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说明佛教如何地与东西方文明互为映照;第一章是“佛教文明的东流”,第二章是“佛教文明的西流”。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佛教的和谐作用”。希望读者在读这一篇文章时有所选择。
第一部分
最早开拓与中亚地区往来的第一位中国皇帝是汉武帝;据《史记》记载,汉武帝第一次(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到张骞从西域逃回来向武帝复命,总共花了13年,其中被匈奴人囚禁10多年,假如不是匈奴自己内乱,张骞差一点就没命逃回来。
西域指的是现在甘肃敦煌以西、天山南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及中亚一带。到公元前115年第二次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才打通了中亚、南欧和北非的经济往来,这条通道,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
1.1 佛教的缘起,
佛教是在公元前6-5世纪,由当时印度小国迦毗罗卫国的一位太子悉达多一人开始;悉达多太子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对于古印度文化经典如《奥义书》、《吠陀》更是自小通达;他为了寻求真理而毅然地走出皇宫,遁入丛林,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觉悟后称为佛陀或释迦牟尼,就是觉者的意思。
释迦牟尼将他在菩提树下所悟到宇宙与生命“缘起性空”的“生灭法”,向其门徒在印度恒河中上游宣说49年,到他涅槃之时,已经集聚了为数众多的弟子。在他入灭之后的两、三百年,阿育王(公元前273-232年)在印度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叫做“孔雀王朝”,并把佛教传播到印度各地和比邻印度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据阿育王时期的碑文《摩崖法敕》(第十三)记载,佛教传教师的足迹甚至远及安息、大夏、埃及和希腊。
也就是说,从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佛教不仅从恒河流域传播到印度全国各地,并进一步传到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由西域一直向东的葱岭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经天山南路二道的龟兹,于阗等国,进玉门关、阳关而传入中国内地。到了贵霜王朝,佛教进一步发展,这时,印度、中亚各地的佛教僧侣经西域各地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内地进行译经与传教。开启了中印之间两千年多年源远流长的友谊。
从阿育王到贵霜王朝,甚至在整个佛教的传播历史过程中,佛教从来没有使用或赞同使用过武力和战争。2004年汤一介教授在“北京论坛”上的讲演《“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中也指出,“印度佛教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外来的印度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从来没有因文化的原因发生过战争,只有三次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有着冲突(本文作者按:应该是四次,即被佛教徒称之为“三武一宗”的“法难”,而不是“冲突”),当时不信佛教的的朝廷对佛教加以打击,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这是任何对中国历史或有基本认识的人都能理解的史实;却有北美科研工作人员仅凭着胡适与许里和的两本书名,就此推论“甚至‘慈悲为怀’的佛教,其传播也离不开武力”;把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这本书的书名当成为“学术结论”,说佛教是以武力征服中国,到其词穷之时,却要求人们与他来确立“武力”的定义。[3]
1.2 佛教的东传
毋庸置疑,佛教东传是古代中印交往的重要内容,它如一轮皎洁明月的月光映照在两国文化的江流之上,由此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交流。最早有传说中白马驮经的摄摩滕及竺法兰,两人皆为中天竺人。到东汉有来自自安息国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还有一大批像鸠摩罗什(公元344至413年),父亲天竺人,母亲龟兹人,支谦,月氏人等西域僧人络绎不绝的到中土宣扬佛法。从以上的这些历史显示,早期的佛教是经过西域以及透过西域人士传来中土,而中土的文化也透过西域传到中亚与欧洲地区,如《奥义书》的地、水、火、风、空(空间的空)的有形物质,在佛教成为“四大”,在古希腊称为“土、水、火、气”。
中印文明互相学习的榜样,也同样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上;罗素在其《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中曾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1.3 牟子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佛教已经开始在社会上流行,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如何接受这一外来文化,印度文明又是如何地与中华文明进行磨合呢?《牟子里惑论》一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概括的轮廓。
据《牟子》自传所述,牟子是苍梧(今广西梧州)人,生在汉灵帝(西元189年)死後的东汉末年。他早年学儒、道学说,不喜兵法,也不信神仙。在牟子的年代,佛教刚传入中国,一般人对佛教多少存有格格不入的意见。因此,牟子在钻研佛学的过程中,常遭到社会人士的不解和非难,认为其所学并不是当时之主流正统文化。牟子“欲争则非道,欲默则不能”,故而牟子用宾主问答的形式,把他学佛的心得写下了,成为这本流传至今的《牟子理惑论》。牟子身为一名居士,他以非凡瞻前的眼光,向后世学佛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初期学佛的艰辛状况,同时也让后世研究佛教的人们能够对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佛教存在中国实际状况有初步的理解。
在《牟子理惑论》中,牟子用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观点、词汇来解释佛教教义,“极力论证佛教的道与儒家、道家的道是相符合的”[4]。有学者认为,牟子的《理惑论》是和原印度佛教的教理有许多不相符之处;这是夫子之见,因为这又何尝不是牟子以佛教的义理在中国随机说法呢!
真理只有一个,佛陀一生随机说法,如当年佛陀遇见善生之子依婆罗门伦理礼拜六方后,向善生子宣说佛法;教导善生之子以圣贤法礼六方之法,并就父(母)子(女)、师生、夫妻、亲友、主仆、僧俗等六种关系[5],指出人际相处之道,这与儒家的“五伦”极为相似。佛陀开示之后,善生子遂三皈依,誓持五戒,成为在家弟子的优婆塞。通过佛陀利用婆罗门的礼拜六方来说法,《佛说善生经》已经成为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可以肯定地说,假如佛陀生长在中国,他也同样会用“五伦”而不是婆罗门礼拜六方来说法。同样的道理,佛教的“四大”来源于《奥义书》的地、水、火、风、空(空间的空),在古希腊称为“土、水、火、气”,佛教以“四大”这个有形的物质来推衍“形而上”之道,假如佛陀生长在中国,他肯定会以“五行”来进行推衍。[6]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之时,曾深思过如何将这不可说(不可以、也无法用人类知见的语言,来说得明白)、不可思议(不可以、也无法用人类的逻辑思维来推理和论议),而必须通过整个身心,经过甚深禅修的“定”学实证所得到无上智慧的佛法传授人间。
佛陀说法49年后,他认为他多年来所说的法的数量只及恒河沙数中爪上的一丁点鸿泥而已,可是世人愚昧,以为能够用世间知见言语入佛观照般若智慧,以为能够以世间所知心来测度如来无上菩提。
正是牟子把佛教的义理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伦理、义理精华相结合,为创立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扎下了理论基础。学术界认为,是牟子的《牟子理惑论》把佛教这一印度宗教文明中国化了。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样评价《牟子理惑论》:“诚佛教之要籍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也说:牟子“调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由此确立了牟子成为将佛教在中国说法的第一在家居士,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确立了牟子成为把印度的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人的地位。
佛教在中国进一步深化的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释、儒、道三家同时并存的文化形态。可惜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把儒家文化当为是中国唯一的传统文化,或最多把道家拿来陪衬一下,完全有意地忽略或抹煞了这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明映照在中国传统文化江流中的地位,抹煞了古今中、印(包括已经不存在的西域)佛教僧侣与在家居士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假如我们把日常许多的习惯用语,如无常、世界、如实、真实、无知、真谛、智慧、观察、心地、觉悟、因果、圆通、平等、自在、心心相印、实际、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这些来自佛教的词汇从我们的语言中抽离。相信现代的中国人将无法完整地讲好一句话。把佛教的雕刻、音乐、建筑、绘画、刺绣、书法………等艺术从中华大地抹掉,中国即使不至于会成为文化沙漠,也必将会失去最辉煌、最灿烂的那一道色彩。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要归功于印度与当时西域的僧人之外,还要归功于那些不辞劳苦的中国僧人如著名的法显、以及历经千辛万苦到印度的那烂陀寺学习的玄奘、玄照、义净、智弘、无行、道希、道生、大乘灯和新罗僧禽业等大师。他们通过讲经、取经、译经,把佛教的文明带到中国来。
第二章 佛教文明的西流
假如我们就东西这两条文明江河向上追溯到公元前6-5世纪,人们会很惊讶的发觉到他们与古印度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条是由古印度产生,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于两汉之间经过西域进入中国,在五百年后与中国的三玄,即《黄老》、《易经》、《庄子》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经过后汉至魏晋约三百年的磨合,形成中国的汉传大乘佛教。再经过两百年后的梁武帝时,菩提达摩由印度东来,传承到慧能大师(公元638-713),最后发展出中国的禅宗思想。2.1 西方的文明
另一条江流则是由
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得经罗马传播到西方世界,也是在约五百年后与希伯来文明形成基督教文化,形成西方社会的一神教文化。又经过约六百年后,伊斯兰教的兴起,虽然这两大宗教与犹太教都拥有类似的《创世纪》故事,拥有一神教的上帝,只因各自拥有不相同的先知,一个是耶稣,正是佛教在两汉之间传入中国的时间,另一个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诞生于7世纪初叶,正是菩提达摩东来传授佛法至慧能确立中国禅宗之时。
由于拥有不同的先知,就有各自不同的圣人与圣地,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圣地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復失地,便对地中海东岸伊斯兰国家发动多次的东征战争。其中的第四次東征是針对其他的天主教派。史称十字军东征(Crusades,1096年—1291年)
从此,这两大文明之间的战斗从未停止过,在这种冲突历史长大的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外界对他“文明的冲突”的置疑,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进一步为西方“新帝国”提供其基本的冲突论述。
相应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适时地提出“和谐世界”的论述以期为世界消弭日渐纷争的不安。截至2006年9月,中国已在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08所孔子学院和12所孔子课堂。2006年4月,《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中国的浙江省举办,其主题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2007年,中国也将举办《首届世界道教论坛》,进一步以中华民族传统主流文化“释、儒、道”向世界宣化和谐力量。
2.2 佛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回到文明的江流,古希腊文明的“土、水、火、气”,没有中国“五行”所能发挥的作用,让古印度的“四大”在中华文明的江流上熠熠生辉,并且最后落地生根。直到十六世纪末,印度的文明才映照在西方这一文化江流上。
所不同的是,佛教思想这一次首先是通过古印度经典与哲学思想传入欧洲。例如,在当时,印度就有人把《奥义书》译成波斯文、蒙古王朝第五世君沙哲汗的长子于1656/7年间命人把包括五十种《奥义书》在内的梵文本翻译成第二个波斯文译本、法国学者杜伯龙(Anquetil Duperron)于1775年带回欧洲与后来又从菽查(Shuja ud Daula)宫庭得到另一个波斯文本,一起翻译成法文。最后于1801/1802年间译成拉丁文才出版了第一卷和第二卷,都是五十种。书名为“古代秘宝”,“印度之古秘密教言,在印度本土亦至为罕见”,以及“中涵神学与哲学理论,摄四《吠陀》之菁华” 。
在文学方面,1808年,德国诗人与印度语言文学家施勒格尔(Fridrich Schlegel)的《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书名所说的“智慧”便是《奥义书》、《薄伽梵歌》和佛教所指的智慧 。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就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出:“那就是我”这句《奥义书》的名言。还有亚倍尔·雷谬莎译的《佛国记》、斯宾斯·哈代的《东方僧侣主义:瞿昙佛创始的托钵僧派述事》、乌布哈姆的《佛教教义》、杜伯龙的《邬布涅伽研究》、德·波利尔夫人的《印度教神话》等。
在哲学方面,威廉·琼斯的《论亚洲哲学》、《印度教戒律纂编或摩奴法典》、哥鲁·布尔克的《印度哲学史》。更多时候,印度与中国哲学是以被批判的形式出现在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历史哲学》等著作里。
2.3 叔本华—西方的牟子
到十九世纪,欧洲出现了类似牟子的近代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公元1788-1860年),他仅能通过上述一点有关佛教的书籍热衷研读,并常在其著作中引述上述书籍的内容与资料;作为一名欧洲的哲学家,他也继承了康德的思想。叔本华以他的意志主义哲学开创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先河,而其理论中心是生成意志痛苦的哲学。其主要的代表作品有1847年的《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及1818年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其哲学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康德,却在意志这里与康德分道扬镳。“康德认为,自在之物只能被想象,而不能被认识。对叔本华来说,这正是康德失败的地方。叔本华宣称,最终有且只有一个自在之物, 我们可以而且确实认识它。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自在之物就是意志”[8]。这是用欧洲的哲学来阐述“远古印度智慧”;中国的牟子是以儒、道思想与古印度佛家思想相糅合。可以这么说,叔本华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时就为现代佛学提供了新的西方哲学素养,成为结合东西文明的西方牟子。
第二部分
第三章 佛教的和谐作用
3.1 “四圣谛” 佛陀第一次说法就是为著名的五比丘宣说“四圣谛”;所谓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而“四圣谛”以及关于人生的三个基本命题“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都在说明人生是苦,无常便是苦。佛陀教导众生的就是如何“灭苦慕道”漫漫的修行正路。
叔本华认为,意志最大的欲求是生命,人的本质便是意志,就是一个攀缘的“行”。哪儿有意志,哪儿就有生命、有世界。人的色身与世界,都是意志的客体化。而人对世间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追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焦虑、无奈、不安、烦恼和苦难(佛教有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取蕴苦等八种苦)都是由意志来的。所以说,意志是人生苦难的泉源。叔本华下结论说:“人生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这与佛家《法华譬喻经》“天下之苦,莫过于有身”、道家《道德经》“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的看法是一致的。
当意志决定了生命时,每一个众生都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而自私自利,以及佛教认为的贪、嗔、痴“三毒”便是一般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这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国际之间的纠纷和世界的战乱。因此,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与世界,就必须要断除人类的意志与烦恼。
2 “十二因缘”
佛家的“十二因缘”为攀缘的“行”即意志作了详尽的分析;生命由“生、住、异、灭”这规律而“出生、发展、变异到入灭”是由“无明”开始;“无明”缘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佛教称之为“十二因缘”的三世二重因果。人生有了意志,就开始会产生“起惑、造业、受生”等一切因果,周而复始的流转,以至无穷。生命就受这“十二因缘”业力无止息的流转,这就是佛教缘起是诸法众缘和合而生的义理,其对治之道称之为“还灭门”。
佛家认为,人的色身及生命的物质是由“四大”组成,“四大”就是“地、水、火、风”。1953 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米勒(Stanley Miller)在无机物中制造出氨基酸(Amino Acid)。我们知道,作为生命最基础的物质是蛋白质,而氨基酸就是蛋白质的基本成分。米勒就在实验室瓶里,放入了水、二氧化硫、甲烷和氨等化合物,这些都是地球初始最多的物质,然后仿造了原始地球自然现象所产生的打雷、闪电、紫外光。经过几个星期之后,试验瓶里产生了包括氨基酸在内的复杂物质。这个实验,完成了由无机物产生有机物的证明。53年过去了,人类对生命起源的探索自米勒的实验后进展缓慢;但是,它还是证明了人类先贤对万物或众生生成的有效观察。科学家认定,要在浩瀚的宇宙星球中寻找生命,“四大”中最重要的“水”是必备的条件,从米勒实验产生有机物的过程中,闪电会产生“火”,打雷产生的气流就是“风”,氨基酸由化学元素组成,我们可以这么说,化学元素表的元素就是“地”的内容。[9]
叔本华在哲学的领域里进一步地阐述,“人的色身是意志的客体化”,认为人有了吃东西的意欲,就会派生出牙齿、食道、胃、肠等相适应的生理器官;有性欲、延续生命的意欲,就会派生出生殖器官;有摄取外物的意欲,就会派生出“六入”(即眼、耳、鼻、舌、身、意)。换句话说,牙齿、食道和肠胃是客体化了的饥饿;生殖器官就是客体化了的性欲。孔子说:“食、色性也”,具体地说明了人的色身是意志的客体化。
意志与生命形式之间的有关问题上,到底存在着怎么样的相互关系呢?即人怎么样会为之人,而万物怎么样会为之万物?目前的科学是无法有力的证明与解释。但是,米勒的人造氨基酸试验,说明佛教提出生命是“四大”因缘和合而生之外,以及提出有情与无情的众生都存在有意志的力量都被叔本华在哲学的领域提出有智慧的研究方向。
即使我们不承认上面的这一段论述,也可以从整个地球生物,包括人类生命的进化史上清楚看到,现今人类与万物生命存在的形式、其生理及心理机能运作形式,强而有力地说明,这些存在的形式,即人有四肢、长颈鹿有长颈、鱼会游水、鸟会飞………就是人类与众生,在适应社会生活环境,以及百万年来与大自然生活环境顽强搏斗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来的。这种演化过程都记录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这种能够适应地球环境生活与征服环境行为的力量,就是人类与万物的生命意志力。人类包括万物能够在地球上生衍繁殖、演化和生存,都是人类与万物的顽强生命意志力奋发不懈的结果;其中就包含了一种中道的平衡力量。
佛教不只科学地解释了生命的起源,意志也决定了宇宙世界的生成与存在状况,佛家的“业感缘起”认为,众生意志(“行”)的“共同业力”是地球以及宇宙一切有情与无情众生生成的因素,万物能够在地球上以及宇宙各星球能够和谐地运行,都是人类与万物以及宇宙星球的“共业”所造成。它的运作也是无常的,是以“成、住、坏、空”变化可测地运行。无常的意思就是无有常住,它是依循一定的运行规律向前发展,佛家的这种无常观,就是人类和谐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佛教徒认为,世事无常,变幻可测,非佛教徒认为变幻莫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宇宙观。认为莫测的原因,主要是来自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祗的意志在操控众生的命运。假如这至高无上的神祗的意志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那就不能成为万能的神;因为万能就不会受另一种规律力量所左右。假如这至高无上的神祗的意志不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那众生就只能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等待最后审判的日子到来。所以有一句话最能贴切的形容这一情况:“佛教徒怕生,非佛教徒怕死”,因为生即是苦,所以怕生;怕死的原因,是因为死后要等待万能的、不受任何规律所左右的最高神祗的最后审判;即使上到天堂,宇宙万物的生命也只能匍匐在至高无上的神祗意志脚下而已,始终无法获得自在与自由。
怕生就要熄灭意志,怕死就要追逐最高的意志,这是逻辑上的必然,也很容易理解。新教伦理在加尔文提出“增加上帝的荣耀”[10]这一最高的意志追逐,以对抗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西方现代精神文明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否定基督教文明精神;韦伯说这是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神秘观照”力量,在信仰上达到最高的宗教经验,就是与神的“神秘合一”[11]
佛家认为,宇宙世界是由一种称为“微尘”的极微要素在运行,缘起则聚,缘散则灭,一切因缘和合而生。这种极微的运行在《道德经》的第一章也有详细的阐述:“故常无,欲与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个极微要素的运行就是一种“徼”(边际)的力量,我们可以用数学的符号lim△X→0来表示,这是微积分学一个趋近于零的概念,它不是没有,它是一个边际,又有从新开始的意思;任何学习高等数学的中学生都会很清楚微积分学的这一个基本概念。老子要求我们要“观”其“妙”和“观”其“徼”;同时,佛家“止观”的“观”和韦伯所说的“神秘观照”的观也都是“观”,所不同的是佛、道、的“观”是反求诸己、反求诸法,是向内求,而“神秘观照”是要向外求。
万物就在“无”(佛家称之为“空”)中因缘和合而生“妙有”,即佛家所说的“性空缘起”;在缘散之后由“有”进入“徼”(边际)的形态,等待另一次的缘起而从新开始,即佛家所说的“缘起性空”。这也是《愣严经》所说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
这种“无”或空或精神的东西和“有”或物质的东西,都称之为“玄”。也都来源于一个东西,老子把这个东西叫着“道”;佛家在十二因缘里以“无明”来表示。而万物的运行,“有”及“无”的变迁与演化,物质与精神的演化,玄之又玄的变迁又变迁,演化又演化,就是天地万物一切“妙有”的总门。就是生命“十二因缘”的流转再流转,永不停息、轮回的真实写照。这就是“诸行无常”的运行义理。
3.5 中道
龙树菩萨在《中论·观四谛品》对万法的实相写下了一段著名的偈文:“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段偈文正是来自龟兹的鸠摩罗什所译,它具体地说明了佛教的和谐作用。
“万法”,即一切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既然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所以它的存在是假有(不是真假的“假”),即假借一定的条件因缘而存在,因而是无自性、无常、万法皆空、一切皆幻。佛法主张“诸法无我”,所以要消除执著于客观事物的“法执”,不把客观事物当作实有。也要破除把主观的“我”当作实有,破除“我执”,从而达到“心无我”和“法无我”这种“诸法无我”的禅境。“无我”没有否认假有的“我”的存在,而是指万法是无主宰者及无自性。
叔本华批评了以往哲学界观考察世界的思维方式,其中,唯物主义者错误地从客体物质事物出发,把物质当为第一性,从而陷入“法执”。唯心主义者“唯一感兴趣的是从主体出发”,把精神当为第一性,因而陷入了“我执”的迷误。无论是从主体出发或是从客体出发,两派的共同偏颇与盲点之处都是一开始就陷入了它们声称往后所要证明的假设,就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第一性来观察对方,从而双双地陷入了独断论,毫无交集地争论不休。
6 圆满寂静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后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基督教与儒家虽然都扬善去恶,他们也对恶的人心与人性都采取强烈的批判与否定;但是,他们另一方面却各自肯定与追求他们所信仰的终极—“上帝”与“天”;所以,他们最终的努力依然是一种对“上帝”和“天”的意志追求。
基督教对意志的追求,上文已经表过。自“和谐”成为2006年最常见的关键词之后,代表儒家观点的文章主要是在论述“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从而达到儒家的最高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消极的手段[12]。宋儒的代表朱熹,提出要达到这一最高理想必须要做到“格物致知”。所谓“格物”就是穷至事务之理,“穷”理就是上述“徼”或“缘起性空”形而上学的境界,人们很难做到,故退而求其次,就做“致知”,知就是道德的知。
世界各大宗教与宗派思想的伦理道德,都各有各自的律法与禁忌,无非在“致知”的道德上,消极地要求世人要向善及不可做冒犯他人的言语和行为来达到世界的和谐。如儒家的“非礼勿言”等,及佛家的戒律,五戒、八戒等。[13]佛家却能进一步地不执著于“我执”和“法执”,把一切事物看成是虚幻,因而彻底地否定了意志的追求和欲望的满足,最终显现为生命意志的寂灭,达到圆满寂静的涅槃境界。这是和谐世界的实相和最佳写照。而其实证修证“戒、定、慧”的论述,不是这一篇文章所要阐述的。
结语
相信通过上述的介绍,人们应该能够更为了解“自己文化的来源、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生活在当今世界文化潮流中,我们对自己文化应当更有“自知之明”;才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关键的时刻,把握住我们前进的方向。
上个世纪初,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玄学又对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次却来自西方。他们有马克思、康德、叔本华、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影响尤为重大。中国传统思想就此遭到从未有过的冲击,人们一方面渴望接受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启蒙,一方面又担心西方科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从1923年2月开始至1924年底,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一场由人生观引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或“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佛教从这场论争又找到了新的活力,催生了太虚法师(1890—1947年)的“人间佛教”。而社会上一些打着佛教以及儒、道口号的邪门歪道也应运而生,于今发展尤烈,善良的信众们可要小心谨慎地去分辨。2006年的中印友好年,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在印度那烂陀重新启动已经搁置了近50年的修建“玄奘纪念堂”工程,世界各国也争相参与重建那烂陀大学。2006年11月14日,我有幸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由新加坡佛教总会及新加坡外交部协办的“那烂陀—佛教文化联系南亚和东亚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们发言热烈,其中有两个问题发人深省。一、世界上有那么多著名的大学,佛教大学也不少,那烂陀要建立的是一所怎么样的大学?二、“那烂陀大学”已经在12世纪末遭受毁坏,为什么还要在那烂陀原址再建立大学呢?
会后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文章[14]。文章中提到:“佛陀为了寻求真理毅然地走出皇宫,遁入丛林,几经千辛万苦,才在菩提树下悟道。现代佛教是否要由丛林走回皇宫,试图由此就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我认为,这是我们要对上述的两个问题做出回答的思考方向,以及让人深思的地方。”而人间佛教经太虚法师的弟子印顺导师的宣化,已经深入人心;而一生致力于弘扬“人间佛教”及刚在近日“封人”的星云法师,更直接了当的说:“‘人间佛教’的极致就是‘和谐’。”而“和谐世界”将会是解决人类思想纷争以及世界纷争的重要智慧。
综合以上所述,世界文化的两条江流,虽然说要溯本求原,但不能像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说的“轴心时代”那样。因为任何的“轴心”理论,任何的向外求法,最终将导致“文明的冲突”。佛教的思想并不是要把这千江之水汇集成大河;因为江河之水也会有泛滥成灾之日;而是要让世界无数的文明江流,接受无上智慧思想之光的映照,让它熠熠生辉,造福全球各界众生。 “人间佛教”将会是一个无上的智慧供人选择,“千山同一月,万户尽皆春”,这是和谐世界的最真实写照。 于狮城
2007年正月
参考文献
书籍
1.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
2.格桑曲吉嘉措著,达多译。《释迦牟尼大传》,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
3.《善生经》
4.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5.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 1983年3月
6.韦伯著,《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7.S. Jack Odell著,王德岩译,《叔本华》,中华书局,2002
6.南怀瑾著,《中国佛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
7.太虚大师著,《太虚自传》,国营印刷承印,
8.张卫群编译,《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商务印书馆,2003。
9.G.F.穆尔著,郭舜平等译,《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
10.Garry Trompf著,孙善玲译,《宗教的起源》,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11.《法华譬喻经》
12.《愣严经》
13.《佛说八大人觉经》
14. Schopenhauer, A. (1980), “On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5. Schopenhauer, A. (1969),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translated by E.F.J. Payn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报章和月刊
1.新加坡《联合早报》
2.新加坡《南洋佛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