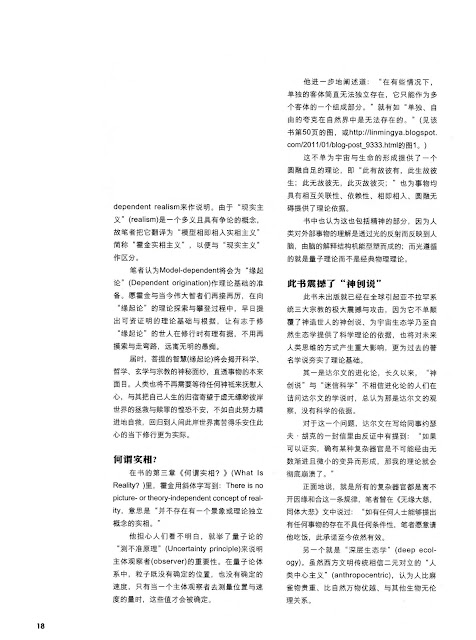美国佛教的传播经验
——李四龙2011年02月09日 世界宗教文化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佛教取得突破性发展,1970年佛教徒人数跃增到20万人,占全美人口的0.1%,实现零的突破。截止2005年,美国人口3亿,佛教徒272万,占总人口的0.9%,接近1%。
这里统计的是正式皈依的佛弟子,若以常理推断,美国还有一批信奉或同情佛教却没有皈依的佛教徒。这个人数,有的估测是达到3500万,美国佛教的类型很齐全,亚洲佛教的诸多宗派,汉传、藏传与南传三大语系的佛教,都在美国拥有道场,已经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这就不得不令我们思考美国佛教的传播经验。
佛教为什么能在美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这与60年代的美国政治环境有关。
1965年移民法案促使亚裔大批地流人美国,这时是美国反主流文化最激进的时期,韩战、越战的相继爆发,为佛教在美国的迅速传播创造了契机:亚裔带来了佛教,欧裔美国人则想了解佛教。但是,这只是美国佛教发展的外部条件,而其深层的原因是,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对亚洲佛教的期待。
60年代以来,美国孕育了一种“美国化了的佛教”,或许能为亚洲佛教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经验。
美国佛教的特色有三点:世俗佛教、世界佛教和参与佛教,由此可以探讨传统佛教与西方现代社会相结合的可能性。
一、世俗佛教
民主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这就促使佛教的平等思想要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结合,从而突破亚洲佛教传统的等级观念。
佛教民主化的直接结果,一是僧俗地位的变更,美国佛教的重心落在居士化的佛教实践上,淡化了剃度僧尼所起的作用;从而模糊了僧俗的界限,二是女性在佛教社团里的人数越来越多,有许多妇女取得了佛教社团的领导权。
在中国,僧俗之间的等级秩序清晰可见。美国佛教的民主化,使传统的僧俗体制逐渐淡化,居士、俗人的力量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学佛以后最终出家的例子,在美国并不很多。
譬如在美国的上座部佛教,目前很少有信徒出家为僧。目前在美国传法的欧裔大乘佛教徒,大多继承日本佛教的衣钵,有家有室,蓄妻生子。
“独身”的观念,在当前的美国社会不再被认为是宗教虔诚的标志。因此,美国的僧人,是在寺庙或禅修中心“指导”信徒,很难成为信徒们永远的老师。这就与亚洲僧人不同,他们在居士面前享有崇高的优越地位。
但美国的居士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希望能对佛法有直接的了解与体悟。当然,在较为单纯的亚裔佛教社团里,僧宝的优越地位仍还十分明显。
同时,美国的信仰格局,相对于天主教国家,更能契合大乘佛教的理念。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并不以成佛为目标,学佛的最高目标是成就阿罗汉果位,佛与学佛者之间有距离,但在大乘佛教,消除了这种距离感。
大乘佛教强调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相即不二,就像禅宗常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并不区分神圣与世俗的领地,天上与人间并无必然的圣凡关系,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乘佛教的这种不二思想,与美国社会的世俗主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使大乘佛教在美国获得了发展空间,也使美国的佛教具有世俗主义的特色,出现了在家信徒日益增长而出家僧人并不见多的局面。
台湾佛光山在美国有多家道场,每个道场的出家众并不多,但是每个道场都有由众多在家信徒组成的国际佛光会护持。这种传播模式所推动的居士佛教,其领导权仍在出家众,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并没有削弱僧宝的地位,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很好的连续性。
因此,美国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培育了一种新型的居士佛教。佛教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
二、世界佛教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种族问题,长期困扰着美国社会。不同的种族,通常具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因此,佛教在美国的传播首先就会遇到种族问题,佛教徒的肤色连带着他们会有不同的文化需求与社会心理。以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美国社会,必须找到能协调国内多种族、多宗教问题的有效途径。
这就诞生了“多元主义” (pluralism)的主流价值,普遍承认各宗教的存在意义,推行“宗教多元主义”(religious pluralism),鼓励宗教对话。在这样的环境里,亚洲佛教必须转变为“世界佛教”。这并不因为美国拥有亚洲各种佛教形态,而是美国的佛教需要找到自己的普世性。
哈佛大学的印度学教授德安娜(DianaL.Eck),既在大学里开设“世界宗教:多样性与对话”这样的课程,又在出版专著,影响美国人去突破基督教的单边主义。
她提醒大家,在当前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印度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意味着什么?各宗教的信徒首先是如何弥合宗教内部的分歧,其次是如何在更大的范围考虑宗教的多样性。哈佛大学神学院也在冲破重重阻力以后,成立“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德安娜1998年在为《美国佛教》撰写的前言里,以旧金山湾区密集的宗教社团为例,解释了推行“宗教多元主义”的必要性。
截止1997年,湾区150多座佛教道场,有上座部的,也有藏传的与汉传的佛庙,汉传的大乘道场还分中国与日本,日本的还分禅宗与净土真宗等:此外还有印度教、锡克教、耆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面对如此丰富的宗教多样性,若是推行单边主义,势必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因此,宗教对话成为一种大势所趋,也是美国佛教徒与佛教学者共同面对的时代主题。
就目前而言,美国佛教的对话对象主要是基督教,以佛教——基督教为主体的宗教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最为显著。
在东西方宗教交流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美国夏威夷大学,自1981年起编辑出版《佛教——基督教研究》的年刊,隶属于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宗教计划” (East-West Religious Project)。
这场对话,在西方已成显学,美国还设有“佛基研究会” (Society for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从铃木大拙的时代即已开始。而到60年代,天主教“梵二”会议召开以后,“宗教对话”在基督教世界已被普遍认可。在这场对话中,美国的宗教学者意在能让佛教与基督教彼此受益。
1986年英格拉姆(Paul lngram)与斯特伦(FriederickStreng)出版《佛教——基督教对话:彼此的复兴与转型》,颇能彰显这种“双赢”的意图。
1990年科比(John B.Cobb)发表《空的上帝:佛教——犹太教基督教的对话》,1998年他还发表《超越对话:朝向佛教与基督教的彼此转型》,这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与京都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阿部正雄,一直引领北美地区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
目前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与博士学位论文,都已相当丰富,互联网上甚至还有这方面的主题书目。
“基督禅”的提出与发展,堪称是这场宗教对话最成功的实例。1971年天主教神父乔史顿提出“基督禅” (Christian Zen)的想法,借用佛教的“禅法”服务于基督徒的灵修。它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数息”的方法达到止观的禅境,观想天主,在心灵深处见到天主,与天主结合为一,顿悟“天主是爱”。 “基督禅”这个概念一经提出,随后受到了佛教与基督教共同的欢迎。像“基督徒能否成为佛教徒”、 “佛教徒能否成为基督徒”这样的问题,也就随之消解。基督禅的实践,对美国佛教今后的发展或许会有持续的影响。因为禅宗在美国的发展势头还在继续,美国的禅未必需要模仿东方的禅。
在美国的多元宗教文化环境里,亚洲佛教成了一种地道的“世界佛教”:超越民族的局限性而显现跨民族、跨文化的普世性。
美国佛教的普世性,更多的是体现在所谓“参与佛教”的理念里。
佛教与基督教的思想互动,基督教向佛教学习禅观冥想的方法,而美国佛教亦在参照基督教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诸如“社会正义”、 “临终关怀”等。西方世界因此又有“参与佛教”的提法,类似于我们所说的“人间佛教”。
三、参与佛教
从越南到西方弘法的一行禅师,1966年成立了“相即社” (Tiep Hien Order,Order Of Interbeing),并以越南语表述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四字。
而用英语表达时,一行禅师最早采用了Engaged Buddhism这个短语。太虚“人间佛教”的提法,最初源自他的“人生佛教”。因此,“参与佛教”主要是说,佛教要为现实人生服务,强调佛教徒在家庭与社团里的责任。
现在,“参与佛教”已被看成是当代欧美佛教的普遍特征。它的含义主要是,佛教需要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譬如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临终关怀、女性解放、国际难民,乃至日趋严重的恐怖事件等社会问题。当前的美国佛教,被认为最能体现“参与佛教”的特征。
1996年的《参与佛教:亚洲佛教解放运动》、2000年的《西方的参与佛教》,这两部论文集分别介绍亚洲与西方的“参与佛教”,解释“参与佛教”的形成过程与思想资源。
前一部论文,介绍亚洲佛教参与社会的实例,主要包括:印度阿姆贝塔(Bhimrao Ambedkar,1891-1956)、斯里兰卡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1864-1933)的佛教复兴,以及一行禅师、创价学会的弘法实践。
后一部论文集,主要介绍西方“参与佛教”的弘法理念、实践与特色,涉及美国“创价学会的种族多样性”、“佛教环境行动论”、 “妇女在美国佛教的主动性”、 “同性恋的佛教”、 “多伦多亚洲佛教徒的社会行动”等。
美国佛教的参与人世,包括“家庭化” (domestication)与“政治化”(politicization)两个层面。也就是说,既有“人间佛教”服务于现实人生的宗教诉求,还有“参与佛教”涉及社会层面的政治诉求。但这种政治诉求的实现,依靠各种途径的对话来达到符合佛教精神的“普世伦理”。
所以,“参与佛教”内在的精神动力,是要构建所谓的“佛教伦理学”:佛教如何能对多元主义的美国社会有益?
佛教伦理学在美国的时兴,正是体现了佛教在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积极功效的可能性,运用佛教的古老原则来处理现代社会的崭新话题。
这些年,美国的大学也给本科生开设佛教伦理学的课程,已有多部以“佛教伦理学”为题的教材。譬如,关大敏(Damien Keown)以研究佛教伦理学著名,他在1992年出版《佛教伦理学基础》。
出于对佛教伦理学的关心,他与普莱比什(Charles Prebish)在1994年创办了电子期刊《佛教伦理学报》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佛教伦理学,当然是要处理各种世俗问题,诸如财富、生命,生态等,这是“参与佛教”必然要去面对的问题。1990年史威乐(Donald Swearer)等编的《伦理学、财富与解脱:佛教社会伦理学研究》,对此有所说明。
1992年拉夫洛(William LaFleur)发表《液体的生命:日本的堕胎与佛教》,讨论佛教卷入日本有关堕胎辩论的前后经过,涉及到有关纪念流产胎儿的佛教实践问题。1997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佛教与生态学》,可以说是首次全面考察佛教的生态伦理。
美国佛教的女性化现象,本身需要构建一种佛教伦理学予以新的解释。自古以来,女性在佛教徒里的比重向来很高,而在出家众里女性的比例并不太高。但是,美国佛教的女性化倾向很明显,不仅是信徒,而且是出家的女众越来越多,这几乎成了一个潮流。
在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里,美国妇女占据关键的领导岗位。而在欧裔的佛教社团里,女性化更加显著。美国佛教学者,尤其是研究藏传佛教的学者,很重视女性在佛教里的地位与价值,出现“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
当然,世俗佛教、世界佛教、参与佛教,上述三点的归纳,只能反映美国佛教的部分传播经验。佛教要在美国的多元宗教环境、在强势的超级大国里传播,必须学会适应美国的社会与文化,创造出一种“新佛教”,这既不是简单地改变亚洲的佛教传统,也不能简单地去迎合美国的文化需求。
美国佛教的这种主动调适,促成了“新佛教”的基本理念。因此颇能体现全球化时代的佛教理念。
当前西方的佛教,试图融合南传上座部的禅观体系、汉传大乘与藏传金刚乘的修行理论,有的还独树一帜,标榜自己属于“第四乘”,即在小乘、大乘与金刚乘以后的最新发展。美国佛教的实践,或许就是“第四乘佛教”,注重禅修、强调参与,倡导宗教对话,是契合现代西方社会的新佛教。
作者:李四龙
作者:李四龙